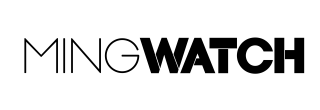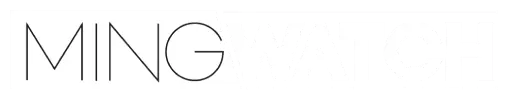「一部電影成功,並不只是劇情如何,而是它如何觸動你的情緒。」電影美術及服裝指導張蚊(Irving Cheung)在訪談中回顧自己對舊香港電影的熱愛,如何從美術與服裝工作出發,逐步發展成為能以影像表達內心世界的創作者。從攝影黑房到MV拍攝,她的藝術視野與電影實踐交織,讓每一格影像都成為一張細膩的照片。
photo: KI
Wardrobes by Longchamp
MAKEUP / @make_upbynichol.c
童年影像與藝術啟蒙
張蚊的電影世界觀源自童年的影像經驗。自小就赴英國留學,姐姐是她進入電影世界的啟蒙者,跟隨姐姐拍攝影片長期做免費勞工,她形容當時的生活極度單純,沒有快餐店,房子甚至沒有電梯,卻與片場的高壓環境形成鮮明對比。這段經歷培養了她對影像細節與空間感的敏感度,也讓她在日後的美術指導工作中,能精準把握每一個細節。
張蚊回憶起自己最早被吸引的舊香港電影,是王家衛的《花樣年華》。她在倫敦修讀藝術期間,曾在Curzon Soho獨立劇院工作,這家戲院專門放映外國藝術電影。「我瘋狂看《花樣年華》,不斷在數戲中出現的戲服,當時我就意識到,電影可以每一格都是一張漂亮的照片。」在觀影過程體會到電影除了技術與流程,更能作為藝術的載體,呈現每個細節與光影的美感。
從美術服裝到導演視野
張蚊畢業回港後,曾短暫從事CG工作,隨後師承電影美術總監張世宏,從助理美術、服裝做起。「我在現場培養出本能直覺,比如演員出汗時補妝,器材如何安置,這些都是現場美術與服裝的敏感度。」多年後,她開始思考導演的可能性。「在取得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藝術碩士學位之後,我的老師點醒我,既然學了十幾二十年電影,為何不嘗試用導演這個媒介表達想做的事情?」疫情期間,即使沒有戲開,她亦利用拍攝MV與短片練習導演技巧,逐步培養對演員與畫面的直覺判斷。
電影的情感與畫面感
張蚊認為,電影最動人的不是劇情,而是觸動觀眾的情緒。「小時候我喜歡看對白與畫面,每格都很精緻。長大後再看,帶著人生經驗,感受會更深。」她特別欣賞能以視覺與節奏操作觀眾情緒的作品,即使是極端劇情,也能呈現獨特的電影語言。她指出,舊香港電影因拍攝工具與技術限制,常常要即興處理「錯誤」,這些意外反而成為創作的養分。「你接受了錯誤,利用它,故事會變得更好,影像會更有生命。」
《空手道》(2017)
隨緣與化學作用——創作中的即興美學
張蚊強調,現代拍攝雖有更多數位選擇,但她偏好現場的「隨緣化學作用」。「遇到演員當天的心情,未必按計劃演出,反而可能更有趣。」她將這種不確定性視為美術、服裝與導演工作的核心哲學,讓每個細節都自然融入故事,形成獨特的影像張力。「成功的電影,讓你不只記住劇情,而是那份情感、那種感受,好像你真的經歷過。」
《年少日記》劇照
影像背後的責任感,用巧思創造電影世界
「美術指導不只是決定畫面的色彩與布置,更是整個電影世界的塑造者。」她分享對電影美術與服裝設計的理解,從場景選擇、色彩調控到氛圍營造,每一個決策都關乎電影的整體感受,也影響觀眾的情緒與代入感。「美術指導的職責遠超於視覺呈現,任何你看到的畫面,你決定放什麼入鏡,你決定當時沒資源的做法。」即使預算有限,也能透過巧思打造具有一致性的電影空間。她提到拍攝雲翔導演的第五部作品《遊》時,戲中涉及七個國家,不同時代與環境交錯。「我想用一個靈性的元素貫穿故事,例如聲音,蒙古包門口的鈴鐺、荷蘭農場的風鈴,讓觀眾在視覺上連貫地感受角色的情緒。」在另一部低預算電影中,她透過隧道、天橋與屋邨小景創造空間感。「即便場景簡單,也能藉由攝影構圖、光影安排形成完整的世界觀。」這些都是美術指導在拍攝前就需要考慮的複雜設計工作。
《遊》劇照
港產片的口味轉變
張蚊回顧港產片的演變,過去十多年,香港觀眾的電影偏好逐漸改變。「十多年前,我問一位前輩監製,現在什麼戲能賣座?他只回答警匪片和戲劇。那段時間,警匪片仍然是主流,但觀眾也逐漸對溫情題材有需求。」她認為,電影題材的變化往往與製作預算密切相關。「當你沒有預算,無法拍昂貴場景,你就會開始描寫自己熟悉的生活,寫身邊的故事。」這種現實限制反而促成了更多創意,讓編劇與導演從生活經驗中尋找靈感。
《飯戲攻心》(2022)
編劇與導演的角色變化
在她看來,近年的港產片製作環境也促使更多編劇自我轉型為導演。「因為如果導演不懂得自己寫劇本,就很難拿到資金,懂得寫的編劇卻有機會推銷自己的故事。」她自身也在疫情期間獲得朋友協助,把自己的構想轉化成完整劇本,才能完成首部劇情作品。「交換吧,我做美術,你幫我寫劇本,互相扶持,才得以完成這個故事。」
年輕觀眾與舊港片的情感連結
對於00後觀眾,張蚊認為他們仍然會懷舊,但對藝術電影的關注有限。「他們會瘋狂看《殭屍》、周星馳的作品,但更藝術、復古的港片則相對陌生。」在她與學生互動中發現,舊港片的情感和故事形式仍有價值,但觀眾的接受度受時代影響。她也回想自己童年在戲院的觀影經驗,《阿郎的故事》、《秋天的童話》等電影深深烙印在心。「小時候看電影,哭到瘋了,但當時未懂得從技術角度欣賞,只是感受情緒。」以至影響到她的取態,並非技術至上,而是依靠感受與幻想力。「我專注於氛圍,用整個畫面去衡量角色與服裝、顏色、光影,讓每個元素服從故事需求。」對於過往作品,她坦言沒有一部作品能稱為滿意,但有些滿足之處。「例如《年少日記》,資金極為有限,但依然營造了完整氛圍,這種對比感讓我覺得自己還做得不錯。」
《殭屍》劇照
香港電影的精神
「香港電影的精神,是一種軍心——全組人為了畫面、為了導演不顧一切。」張蚊用一句話形容香港電影精神,她解釋這種精神使團隊能在有限資源下完成創作,維持高效率與協作力。「即便沒有足夠預算,大家也會互相支持,為畫面達成共識。這種集體力量和忠誠感,使香港電影擁有獨特的文化印記,也是這個行業持續吸引人的核心魅力。」